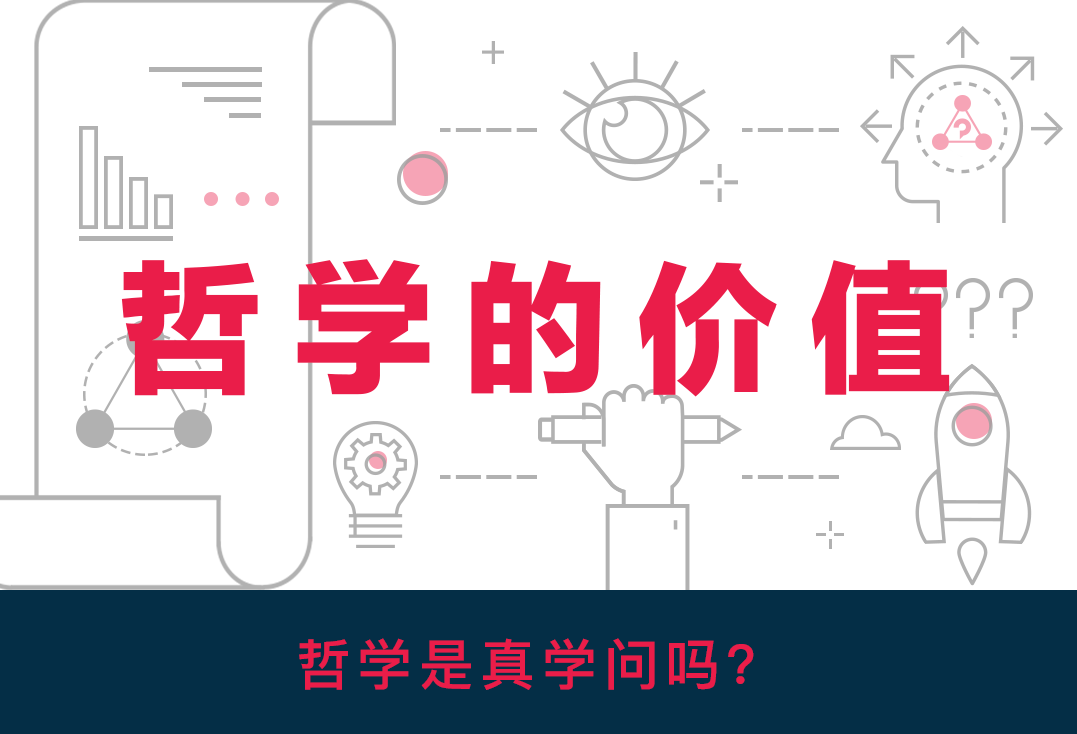
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哲学是一门真学问吗?
哲学似乎从未产生过任何知识,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从未给我们提供过任何确定的正确答案。对于任何哲学大问题,从来都是一帮哲学家在那吵来吵去,从三千年前开始就是这样了,哲学就一直没产出过任何确定的知识。试问,屏幕前的你能说出任何一条确定的哲学知识吗?
我们说一门学问是不是真学问,主要看两个标准,一是看这门学问有没有提供正确答案,二是看它有没有在发展进步。
我们先看第一条。所谓学问,有学就有问,而有问就必有答。一门学科如果是真学问的话,它就必须就它所研究的问题,提供一个正确答案,这个正确答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真学问要产生知识。但是,这个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却从未给我们提供过任何确定的正确答案。
比如说,你上完一堂物理课,你下课以后走出教室就可以说:今天我学到了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是相互吸引的!你上完一堂生物课,你下课以后走出教室就可以说:今天我学到了我是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你上完一堂经济学课,你下课以后走出教室就可以说:今天我学到了价格越低需求就越大!但是,你上完一堂哲学课,你走出教室,你发现你只能说:今天我学到了几派互相对立的哲学观点。但是你问老师这几个派别到底哪个是对的?老师最后说: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
哲学不像其他学科,对于所谓的哲学问题,也就是我们这里常说的「大问题」,都给不出任何确定的正确答案,比如说「人有自由意志吗?」(Free Will)这个哲学大问题,拉普拉斯说,人没有自由意志,罗伯特·凯恩说,人有自由意志,哈里·法兰克福说,人既有自由意志又没有自由意志。这三种回答,各路哲学家各说各话,好像还都挺有道理,但是就是莫衷一是,达不成共识。
再比如说,「心灵和身体是什么关系」这个哲学大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心身关系问题」(Mind-Body Problem)。笛卡尔说,心灵实体是独立于物质实体的另一种实体;弗兰克·杰克逊说,心灵是物质的副现象;吉尔伯特·赖尔说,要把所谓的心灵实体都转译为行为表现;UT普莱斯说,人的心灵状态其实也就是人的大脑在放电;丘奇兰德夫妇说,根本没有心灵状态,心灵都是错觉;希拉里·普特南说,心灵状态是一种可多重实现的功能状态,大卫·查尔莫斯说,心灵状态是独立于物理状态的另一种物质实体的属性……总之关于这个心身问题,哲学家们是吵得不可开交。好多哲学家,包括卢梭、恩格斯都说过,类似于心身关系这样的问题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问题,那么关于这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有确定的正确的答案吗?没有。那关于一个学科如此重要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正确答案的话,这门学科还算是真学问吗?
刚刚我们只是举了两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来做例子。可以说,绝大部分哲学问题,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哲学家们各说各话,没有确定的答案。你要是说,我们哲学和文学和艺术一样,无所谓正确答案,所谓文无第一,我们和文学艺术一样,本来就不产生知识,我们主打一个提供审美和情绪价值!这么说也不会产生很大的争议。但是偏偏哲学家又标榜自己和文学艺术不一样,是产生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是研究真理的,我们研究的真理甚至比科学更是真理!那我们自然会问:你都说你是产生知识的了,是研究真理的了,那你倒是告诉我一条确定的哲学知识?
说哲学不是一门真学问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这门学科没有累进性,也就是说哲学史发展好几千年并没有什么进步。
我们先看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完全错误地说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到今天的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今天的物理学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物理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物理学在进步。
化学,从当年的炼金术,发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医药科技,材料科学,能源技术,都有现代化学的重大贡献,比起当年的炼金术,化学在进步。
不光是理科,文科也在进步。比如说历史学,孔子时代的人对于上古三代的了解,更多也只是基于一些传说,但现在的历史学家对于夏商周的了解,基于文献研究和考古发现,肯定是比孔子时代的人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真相,历史学在进步。
但现在来看哲学,我们会发现,当代哲学家研究的那些哲学问题,包括刚刚说的自由意志问题,心身关系问题,以及什么自我同一性问题,他心问题,上帝问题,不能自制问题,缸中之脑问题等等等等,这些哲学问题,这些所谓的前沿哲学问题,其实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那个时代都已经在研究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当代哲学家都还在研究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前的哲学问题,还在为老掉牙的哲学问题争论不休。这就相当于什么?就是一个当代的化学家,居然有大学雇佣他给他发经费研究炼金术。
而且,当代很多哲学家做的工作就是阐释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现在有哪个哲学家,敢声称自己的哲学水平,超过了柏拉图、超过了黑格尔?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过:「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这听起来好像哲学很厉害的样子,很多当代哲学家还为此沾沾自喜,说自己在研究经典。但是,这恰恰不就说明了,这么多年来哲学一直在炒冷饭?
如果三千年前人们研究这个学问和三千年后人们研究这个学问还是同样的水平,那这门学科就没有进步。这研究了三千年,养活这么多靠这门学科吃饭的人,那这不就是浪费科研经费吗?这哲学研究了三千年,换了不知多少哲学家,但改过了吗?给出了哲学问题的确定答案了吗?换汤不换药啊。
当然,这也是咱们《大问题Dialectic》节目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哲学家辩论的节目形式,并不是咱们为了节目效果,故意不提供最终的确定答案,而要往辩论赛这种节目形式硬凑。真的就是哲学就是如此的!对于各种大问题,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真的没达成什么共识。
同理,对于「哲学是真学问吗?」这个大问题,哲学家们也没达成共识。一些哲学家们持悲观态度,正如之前说的,他们认为哲学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提供任何正确答案,没有发展进步,因而不是真学问。但也另有一些哲学家们持乐观态度,认为哲学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答案,其实有在发展进步,因而是一门真学问。那么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四个派别的哲学家来探讨争论「哲学是真学问吗?」这个大问题。他们分别是,以纽约大学的哲学家大卫·查尔莫斯为代表的激进悲观派,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哲学家丹尼尔·斯图尔加为代表的温和乐观派,以利兹大学的哲学家海伦·毕比为代表的温和悲观派,以及以香港大学的哲学家赫尔曼·卡佩伦为代表的激进乐观派。他们将会发表他们对「哲学是真学问吗?」这个大问题的论证,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他们的看法有没有道理。
1、大卫·查尔莫斯——激进悲观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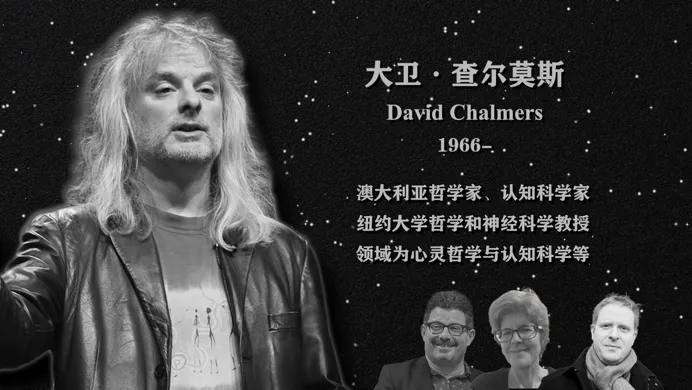
2、丹尼尔·斯图尔加——温和乐观派

3、海伦·毕比——温和悲观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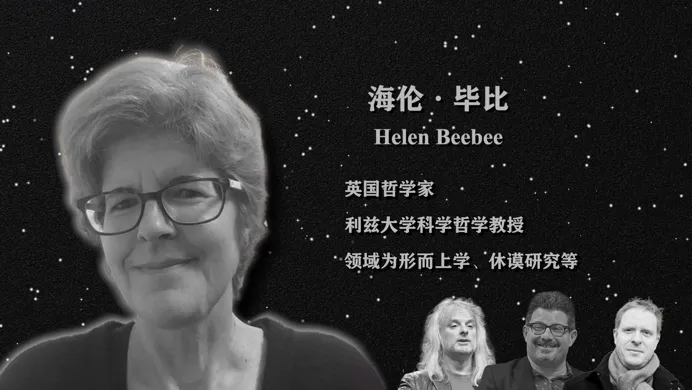
4、赫尔曼·卡佩伦——激进乐观派

大卫·查尔莫斯——激进悲观派
关于哲学是否是真学问的大问题,最激进的悲观立场当然就是认为哲学完全不是真学问,完全没有进步。而支持这种立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问题有一致的、得到广泛共识的回答。这个我们在开题时候已经提到过一些了,也就是说,哲学家之间,对于每个哲学问题,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这个立场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澳大利亚哲学家、纽约大学的哲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大卫·查尔莫斯,我们在之前的很多期大问题节目里都见过他。他自己就搞了个调研。他统计了四百五十多名专业的哲学家的哲学观点,问了他们30个在哲学界内特别重要的哲学大问题,比如心身关系,比如自由意志这种大问题。结果30个问题里面,有23个问题,支持人数最多的立场,还不到总人数60%。(调研链接:https://survey2020.philpeople.org/)
支持人数最多的立场还不到60%,这应该如何理解?这就相当于,你问现在的物理学家,牛顿力学在微观高速情况下还适用吗?然后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告诉你:不适用;剩下的一半物理学家都告诉你:适用,适用得可好了!再或者,你去问化学家:砒霜能让你长生不老吗?有一半左右的化学家都告诉你:能!砒霜是活血化淤、延年益寿的宝物!你看看,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形,放在任何学科上绝对是一个灾难。
但是在哲学上,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太常见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之前也提到过,心身关系是一个特别古老的问题了,但现在?最主流的理论是物理主义,这个物理主义我们就简单理解为结合现代科学版本的唯物主义吧,但这个主流理论的支持者只有52%,换言之,有接近一半的哲学家都觉得它是错的。这就很可怕了!我们直到现在,还在纠结几千年的哲学问题,而且还根本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这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人类的哲学界这个整体,没有产生任何知识,因为他们没有一致的信念。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一件事情具有知识的前提是对它具有信念,但是具有信念还够不上就具有了知识,还得是人与人之间关于这件事情的信念是共识性的信念,尤其专家学者之间对于这件事情具有共识性的信念。而哲学家这个群体根本没什么实质性的共识,所以哲学家们根本就没有发现或贡献出任何哲学知识。他们就连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都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你都没提供过任何一个哲学知识,哲学哪里算得上是真学问?这种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的状况,就搞得哲学家们一个个的,对于自己的观点特别自信。就比如说自由意志问题,哲学家A认为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凭什么相信有自由意志?在面对其他同样厉害的哲学家的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凭什么就这么笃定你坚持的观点就是对的?
我们看其他学科,比如说你是一个天文学家,你在计算一个小行星多久会撞地球。你算的结果是:还有2年半。然后,有一个和你差不多一样厉害的天文学家,水平也很高,所用的观测数据也和你一样,他也算这个小行星多久撞地球,算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还有2个月。那这个时候,哪怕真的是你算对了,你也没理由特别自信的说你就是对的,他就是错的。他水平、能力、掌握的证据、工作的态度都不比你差,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先悬置你的自信,你们互相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谁算错了,最后你们都发现,比如说是他算错了,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敢确定「小行星还有2年半撞地球」这个知识。
但是在哲学圈搞哲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假设你认为自由意志存在,但是有那么多哲学家认为自由意志不存在。这些人可一点不比你傻,一点不比你笨,也一点不比你懒。那你凭什么相信自由意志存在?你的这个观点能得到辩护吗?很遗憾,不能。但是哲学家们通常都会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自己说的就是对的,自由意志就是存在。
这种迷之自信,根本不管业界其他学者的不同观点的人,放在科学圈,可能甚至被叫做民科,也就是民间科学家。就是成天在自家小书房里面,在那想、算,根本不去参考学术圈同行的不同观点,自行其是,发明出自己独特且奇怪的理论。这就是民科。那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做哲学,就相当于民间科学家搞科学。那你能说哲学是一门真学问吗?
总而言之,激进悲观派认为,哲学家之间在几乎所有哲学问题上,都有着极其明显的分歧,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因而哲学这门学科就没有产生任何知识。哲学家们一直在同样的问题上吵来吵去、争论不休,不停地炒冷饭,一直在原地踏步。套用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的话说:
在一代人中流行的臆测在下一代人眼中成了不可理喻的错误,而在第三代人眼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也许还给人一种“这是重大新发现”的感觉。
——《哲学研究的进步状况》
丹尼尔·斯图尔加——温和乐观派
哲学家丹尼尔·斯图尔加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哲学是一门真学问,因为哲学确实已经解决了一些很重要的,曾经人们特别关心的大问题!之前古人提出的哲学问题,我们很多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斯图尔加就举了之前提到过的心身关系问题的例子。我们要知道,心身关系问题乍一看是在笛卡尔那个时代就在讨论了,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其实不然。今天的我们关心的心身关系问题,已经是和笛卡尔关心的不同的问题了。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笛卡尔追问的是心身关系问题,我们追问的也是心身关系问题,哪里不一样了?注意,这只能说明你们关注的话题一样,而不能说明在这个话题里,你们具体关心的命题、理论是一样的。
关注的话题和以前一样可太正常了,物理学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关注「宇宙的起源是啥」这个大话题了,医学也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关注「怎么治病救人」这个大话题了,这当然不能代表物理或者医学没有进步。它们当然进步,因为他们关注的具体的理论和命题已经变了。比如说,以前人们觉得这个宇宙就是上帝造的,或者盘古开的,而现在人们觉得是宇宙大爆炸。医学也类似,以前人们觉得吃某些毒药可以治病,现在人们开始使用青霉素了。所以说,虽然我们延续了共同的话题,也就是「宇宙的起源是啥」、「怎么治病救人」,这些话题没有变;但是我们更新了我们的理论,我们更新了对这个话题的具体的回答。
斯图尔加认为,哲学也是一样,我们继承了心身关系问题这么个大问题、大话题,但是我们已经更新了具体的理论和回答,我们也给出了不一样的命题。具体而言,笛卡尔那个时代纠结的问题是什么,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六沉思写的很清楚,他关注的是,如果有心理上的事实,那是不是所有心理上的事实都是广延性的事实?这个广延,简单说就是占据物理空间的意思,也就是有长宽高。所以这个问题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有心理上的事实的话,那是不是所有这种心理事实都是关于物理上有长宽高的东西?我们现在当然会回答:不是!有太多心理事实和广延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我现在在幻想自己吃火锅」这个心理事实,它有长宽高一说吗?显然没有!这在现在完全就是哲学家和普通人都承认的常识,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笛卡尔当年的哲学贡献。
要知道,在笛卡尔之前,人们可没这种常识;但是在笛卡尔之后,人们都接受了这个真理。笛卡尔当初可是为这件我们现在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做了很严肃的论证的,他的论证就和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总而言之,笛卡尔的这个说法被人们逐渐一点点采纳,成为了大家公认的真理,这完全就是哲学的贡献!也正因为他的贡献,我们现代的心灵哲学就不再关心笛卡尔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了,转而去关心更加复杂的问题,比如给定了一切物理学的事实,我们能不能解释某些特定的心理学事实,比如为什么我们有某些感受质(qualia)。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疼痛感这类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和笛卡尔的那个问题有了天差地别了。
总之,哲学就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我们延续了我们学科的核心关切,延续了一以贯之的大话题,比如怎样才是道德的,比如心身关系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已经成功回答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新的问题与理论。人们之所以有哲学好像没有在进步的错觉,正是因为那些被成功回答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迅速就不再关注了。笛卡尔解决了他的问题,我们后世的哲学家就没法针对同样的问题再发论文了。哲学家们那,永远只关注那些还没有被回答的,还有待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才搞得哲学家们好像一直都在争论不休的样子。这并不能代表哲学没有进步。恰恰相反,这难道不正体现出我们哲学是一个一直在进步,并且十分低调、谦逊的学科?哲学总是闷声发大财,从来不吹嘘自己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海伦·毕比——温和悲观派
哲学家海伦·毕比认为,哲学算不上真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她是从治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论证这一观点的。
我们都知道,大学里面的所有学科都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对错可言的,一种是没有对错可言的。像物理、化学这种学科就是有对错可言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就叫可证伪。我们知道牛顿力学在一些情况下就是错的,我们知道注射消毒液能消灭新冠也是错的,这是可证伪,有对错的。但像文学、艺术这种学科,很多情况下可能有高下之分,但没有对错可言。比如,你写了一个很难听的旋律,人们会说,你写得很烂,但人们不会说你写错了,不会说「你犯了一个事实性的错误」。
那么,对于像文学艺术这些没有对错可言的学科,它就无所谓有没有进步,或者至少不能用「你发现了多少事实」这个指标来衡量进步。那如果哲学家们认为,我们哲学也和文学艺术一样,无所谓对错,哲学只有境界的高低,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说不着哲学是不是真学问。但是哲学家却偏偏说自己研究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一样,哲学是有对错可言的,我们哲学研究的是真理,甚至是比科学更是真理。
但是,既然你们哲学是有对错可言的学科,那一个有对错可言的学科,总得要告诉我们一些事实吧?你告诉我们事实,我们才好说你说的事实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想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这门学科就得有可靠的方法论(Methodology),让人们能通过这个方法论,来去伪存真,来排除错误的理论,从而发现可靠的事实?
那像物理学、化学这些现代科学,它们的可靠的方法论是什么?那就是科学实验(Experiment)。真学问,得过实证这一关。你说你的科学理论是对的,我说我的科学理论是对的,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通过科学实验这个方法论,我们的各执一词就好解决了:你不是说你说的是对的吗?好,那我做个实验,证明你说的是错的。
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很久以前,物理学还是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很深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越重的物体下降越快。但我们学过高中物理的都知道,物体降速和重量并没有关系。伽利略也这么觉得,他认为亚里士多德肯定在乱讲。那这个时候伽利略是怎么证明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很简单,他走上了比萨斜塔,当然伽利略本人到底有没有做比萨斜塔实验是有争议的,但大体意思是,他做个实验,同时让两个不一样重的球自由落体,结果发现它们同时落地。就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实验,证明了下降速度和重量不是正相关的,这就证伪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我们说回哲学,哲学有没有像科学实验一样的方法?没有!哲学家搞哲学的方法论就是做论证。论证就是从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从而得出一些结论(说到做论证是哲学家的看家功夫,为我们小频道的产品打一个广告,欢迎你报名参加我们制作的《论证与说服50讲》的课程,对我们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论证」即可收到报名链接)。说回来,一个论证想要成立,只有你的前提是对的,你才能说你的论证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问题在于,你前提是从哪里获得的?只是基于直觉!
怎么个叫做基于直觉?我们举例子说,大家都知道,功利主义或者叫做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认为只有快乐才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也就是说,功效主义认为,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之所以有价值,都是因为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或者减少痛苦。那对这个功效主义理论最有名的反驳之一,就是由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做出的「体验机器」(Experience Machine) 论证。大致意思就是说,现在假设有这么一个特别高级的机器,你要是走进这个机器,你就会一直获得最大、最高的快乐,进入这台机器以后,它会给你模拟一切你想要的人生体验,比如你会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或者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并且这体验机器十分高级,你进入机器以后,你会被抹除记忆,你会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个著名作家,那么请问,你愿不愿意永久进入这台体验机器?
诺齐克认为,我们都不会选择进入这台机器,所以功效主义就是错的。因为如果只有快乐是有内在价值的,我们就会进入这台机器,因为这台机器能提供最大的快乐。因此,他得出结论:有价值的不只有快乐。这个论证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
体验机器论证
Experience Machine Argument
前提1:如果只有快乐有内在价值,你就应该进入体验机器。
前提2:你不应该进入体验机器。
结论:因此,有内在价值的不只有快乐。
这个论证非常优美,在很多人看来,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论证的前提,完全就是基于直觉的。比如说,前提2「你不应该进入体验机器」这个判断,我们之所以相信它,完全只是因为它很符合直觉。
但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所有人的直觉,它很可能只符合诺齐克以及一部分人的直觉,真的有不少哲学家,还有普通人(比如我们二次元宅男),他们觉得,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台体验机器,他们肯定特别特别想进入这台机器。
那对于这些二次元宅男来说,诺齐克的这个论证完全就是失败的,因为他的前提2根本就是错的。而问题就在于,这种基于直觉做出的判断的分歧,哲学家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信谁,他们并没有解决这种分歧的方法。哲学家们的直觉是无法调和的。
为什么说哲学家们的直觉无法调和?因为和科学不同,这种哲学家之间的直觉冲突完全不是经验性的,也就是说,完全没办法用经验的手段证实或者证伪。当科学家的直觉出现分歧的时候,那问题就很简单,我们做实验呗,我总可以用实验数据证明你错了。但哲学家之间如何证明对方的直觉错了?你觉得我们不应该进入体验机器,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进入体验机器,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直觉的冲突?我们就只能吵架。
所以,我们说回来,哲学和文学、艺术那些没有对错可言的学科不同,哲学是关心事实,关心真理的,但哲学又和同样关心事实的科学不同,哲学家之间的直觉冲突,没办法用经验性的、实证的方法去验证。而哲学家的直觉,又是受到各种东西影响的,比如自己的受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甚至是恋爱经历,所以根本性的直觉分歧是很难调和的。
而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哲学自身的这种做论证的方法论,永远需要依赖直觉,而直觉的分歧,永远没办法真正消除。所以,哲学不像科学,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论来去伪存真,来取得进步;哲学家永远没办法通过做论证来去伪存真,永远没办法彻底发现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因此,温和悲观派的代表海伦·毕比认为,哲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像科学的那样的进步,因为哲学从方法论上就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确定的正确答案。毕比认为,哲学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可能的答案」。它只能告诉我们,哪些哲学理论「可能是对的」,但因为自身方法论上的局限,它到最后也没法说,到底哪个理论才确定是对的。哲学家能做的,并不是让哲学有什么进步,而只是提出一些经得起反思的、经得起质疑的,可能是正确的理论而已。换言之,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对的,但也不能确定它就是错的,只能说是「如对」。
所以,温和悲观派最终的结论就是,哲学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学问,它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理论、可能的答案而已。其实很多哲学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就像咱们大问题节目,不同的哲学家对一个大问题的回答,你敢说哪个回答就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错的,不能吧,很难的吧,最终都得让各位观众朋友的「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来评比,那各位观众朋友之间比的也是直觉,不同直觉的观众在评论里面,也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不同于激进悲观派的看法,这种观点并不是说哲学完全没办法获得任何答案,而是说它只能获得一大堆可能的答案。就拿本期大问题来说,「哲学是不是真学问」这个大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激进悲观派的观点,可能是温和乐观派的观点,可能是温和悲观派的观点,也可能是激进乐观派的观点,反正都有可能,不确定哪个才是对的,主打个可能性。
赫尔曼·卡佩伦——激进乐观派
哲学家赫尔曼·卡佩伦认为,哲学当然是真学问,哲学其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卡佩伦何以如此乐观?卡佩伦就说,要看哲学有没有进步,我们没必要非得一定从一个人类学的、特别宏大叙事的视角去看,我们不如从最简单的、最微观的视角出发。也就是说,你想想你自己,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在你接触哲学之前,到现在为止,你自己觉得,你在哲学上有没有进步?
比如说,在你12岁的时候,你的哲学知识,和现在,这个已经看完每一期大问题节目以及《论证与说服50讲》的你相比,有没有进步?显然,这个进步可太大了!你以前还不知道怎么做论证,你以前还没意识到时间穿越会遇到祖父悖论,你以前还没想过我自己有可能是缸中之脑。所以很明显,你有进步,我有进步,我们每个看了大问题节目的人都有进步。
所以大家扪心自问,我们自己都学了点哲学,都通过学哲学收获了个人的进步。那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进步,那凭什么能说,我们这个整体会没有进步?这就说不通!这就好像说,我们大家一开始都是文盲,但最终我们都学会了识字,但你却和我说,我们整体的文化水平没有提高,这不是很荒谬吗?同样。既然我们每个个体通过学习哲学、研究哲学都获得了自身的进步,那么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当然也就有进步。
这是卡佩伦给出的第一个论证,就是从每个人自己学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自己确实也通过学哲学收获了个人的进步。如果你没有被这个论证说服,没关系,卡佩伦还有一个更强有力的论证等着你。先说论证的结论,卡佩伦认为,我们哲学界已经找到了几乎所有哲学大问题的正确答案。不同于温和乐观派的斯图尔加认为是回答了一些大问题,激进乐观派的卡佩伦认为,哲学已经找到了几乎所有哲学大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下面卡佩伦就要来证明这一激进的观点了。卡佩伦说,那什么叫找到了答案?就是说,你不但回答了这个大问题,还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证。那你看看,现在还有哪个哲学大问题没有人回答吗?就比如我们这个大问题节目已经更新了五六十个哲学大问题了,每个哲学大问题都有好多个哲学家们来回答。比如我们之前一期,时间穿越是否可能的大问题,一拨哲学家回答可能,另一拨哲学家回答不可能。他们每个人都给出了特别强有力的论证。显然,时间穿越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而对这两个回答,我们都有一大把可靠的论证去支持它们。所以,这个哲学大问题我们就已经找到正确答案了呀!
就拿我们大问题节目的选题来说。我们可以把哲学问题分成两类,一类是yes-or-no类型的问题,比如时间穿越可不可能?比如精神变态杀人是否应当承担道德责任,比如爱情动作片是否伤害了女性,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就两个回答,要么答案是是,要么答案是否。而你发现,任何一个这种yes-or-no的大问题,两种立场都有支持者,而且都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正确答案要么是yes,要么是no,那既然两种答案都给出了,这不就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了?
另一类哲学问题是开放型问题,也就是不仅仅只有yes-or-no两种回答,就比如规范伦理学的「我们应当如何做才是对的」这个大问题,它的答案就不止两种,而是比如功利主义,义务论,以及美德伦理学这几种回答。你要细纠下去,每一派你都能找出来一大摞书,正确答案也就是这些理论中的一种,怎么能说哲学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总而言之,我们大问题节目已经更新的这五六十期大问题的选题,每一期都提供了各路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给出的非常雄辩的回答,把所有可能的答案都说出来了。就拿本期大问题「哲学是不是真学问?」来说,这个大问题的答案,要么就是激进地认为是真学问,要么就是激进地认为不是真学问,要么就是温和地认为是真学问,要么就是温和地认为不是真学问,逻辑上全都包圆了,正确答案必在其中,哪怕正确答案是「哲学不是真学问」,那么关于「哲学是不是真学问?」这个哲学大问题,也是有正确答案的。因此哲学还是真学问。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说了:就算有些人找到了正确答案,也不代表我们知道一期大问题里发言的各路哲学家,哪一个给出答案才是那个正确答案!,你说的没错,但卡佩伦认为,那这就和哲学是不是真学问没关系了。你不知道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答案,不代表哲学家们没有找到正确答案,因此并不代表哲学不是真学问。
卡佩伦做了一个金币类比(Coin Analogy)论证,来论证他这一看法。现在,有人告诉你,我在你家附近1公里藏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金币。然后,你和你家人就出发去分头找这个金币,然后你找到了。当你找到了的那一秒,就算其他人还不知道你已经找到金币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你已经找到金币了。同理,当一个哲学家找到了正确答案,就算其他哲学家还不承认他,甚至就算其他哲学家还不知道他已经找到了,那这些都不影响,他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这个事实。
这个时候,你可能又要说了:等一下,我还是根本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我只是觉得,每一期大问题的各路哲学家说的都很有道理的样子,但每次你夏先生最后都来一句「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我哪儿知道该投哪儿?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哲学家A说完,我觉得说的很对,刚准备投他,哲学家B又说完,我也觉得说的很对,哲学家C又说完,我还是觉得说的很对,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墙头草。所以哪来的正确答案?
卡佩伦说,你又说对了,可这依然和哲学是不是真学问没关系。现在,我们假设有个人告诉你,我在你家附近1公里藏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金币,但我还藏了999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假金币。然后,你和你家人费尽千辛万苦把这1000个金币都找到了,但你们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的金币。这个时候,请问,你们有没有找到真的金币?当然有!你们当然找到了真金币,不仅如此,你们还把真的和假的金币都找到了!,我们还多附赠了999个假金币。你们只是不知道其中哪个是真的而已。同理,我们哲学也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其中哪个是真的而已。所以,既然我们哲学家都已经找到正确答案了,那凭啥还说哲学不是真学问。
卡佩伦的这个论证听起来有点反直觉,我们还是拿咱这个大问题节目来举例。就是说,咱们每一期大问题的选题,尽可能把所有回答都呈现出来了,正确答案必然是其中一个。虽然你看完这期大问题节目,依然不敢笃定哪一个回答是那个正确答案,但这并不能说明哲学不是真学问。这就好像,你看到一期大问题的选题,本来这个问题对你而言是一个主观论述题,你看了一眼题目,觉得毫无头绪,根本不知道从何作答,但是,看了咱们大问题节目以后,各路哲学家纷纷给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那么,原本这个让你毫无头绪的主观论述题,至少变成了一个二选一或者三选一的选择题了。本来一道题你是一分都得不到的,但是,你现在至少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机会能拿分了。当你遇到让你困惑的人生大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看过咱们大问题节目,或者,你学过哲学,虽然你不敢笃定相互争论的哲学家的回答哪个才是正确的,但至少你手握解答人生困惑的选项了。
会议总结
本次研讨会摘要如下:
哲学能提供确定的正确答案吗?
查尔莫斯:哲学家之间从未就哲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哲学从未产生任何确定的知识。
斯图尔加:哲学已经解答了一些具体的哲学问题,因而有在进步。
毕比:哲学从方法论上就无法提供任何确定的正确答案,哲学只能提供一些可能的答案。
卡佩伦:哲学家们把所有可能的答案选项都通过可靠的论证提出来了,正确答案必在其中。
其实今天探讨的这个大问题,哲学是否是真学问,哲学是否有发展进步,这也是另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那就是,哲学是否已经终结了?哲学这门学科,是否还有必要存在?用奥地利裔英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
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这样:除了可以言说的东西之外,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因而也就是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之外,哲学什么也说不了。
——《逻辑哲学论》
关于本期大问题,哲学家们的看法已经发表完了,你觉得哪位哲学家的观点更有道理?你觉得哪一个哲学家提供的答案,对于本期哲学大问题「哲学能提供确定的正确答案吗」是那个正确的答案?最后,咱们还是得以本频道的保留话术来结束本期大问题的探讨: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加入到对本期大问题的探讨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
对上述言论,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
◆Beebee, H. (2018).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and the Aims of Philosoph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18(1), 1-24.
◆Cappelen, H. (2017). Disagreement in Philosophy: An Optimistic Perspective. In G. D’Oro & S. Overgaard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lmers, D. J. (2015). Why Isn’t There More Progress in Philosophy? Philosophy, 90(1), 3-31.
◆Dellsén, F., Lawler, I., & Norton, J. (2022). Thinking about Progress: From Science to Philosophy. Noûs, 56(4), 814-840.
◆Lovejoy, A. (1917) On some conditions of progress in philosophical inquir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26, 123-163.
◆Stoljar, D. (2017). Philosophical Progress: In Defence of a Reasonable Optim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投票

注:投票敬请前往 大问题Dialectic 公众号 原文下进行。
转载请注明:好奇网 » 大问题:哲学是真学问吗?